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8年10月16日,被申请人B工程建设公司向申请人A建筑安装公司发出《重庆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载明中标金额为900万元。10月3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某县示范项目;计划开工日期2018年11月2日,计划竣工日期2019年7月1日;中标价为900万元;第10.1条载明,工程设计变更经项目业主申报审定后,设计变更涉及工程价款调整的,或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有漏项或工程施工中出现新增项目(含招标范围以外的项目),由承包人7天内向发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组织施工项目工程监理方共同审核同意后调整合同价款,上述情况均以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为基础进行比较;第12.4.1条第4款载明,完成结算审计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审定金额的97%,余款3%作为质量保修金,待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后一周内付清,质量保修金不计利息。质保金的支付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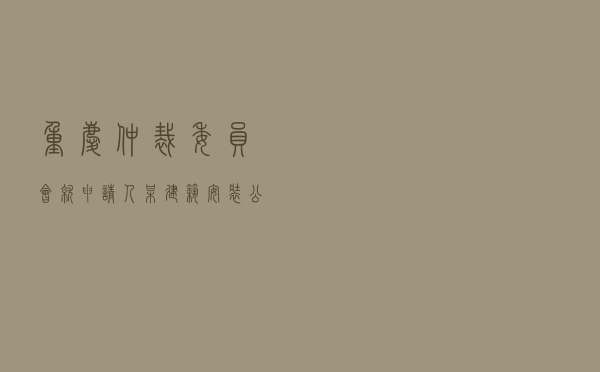
《施工合同》签订后,申请人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被申请人累计支付工程款840万元。
2019年7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了《某县示范片项目结算资料》。结算资料第2页载明,建设单位:A工程建设公司;结算总价:1580万元;申请人加盖了一枚公章;被申请人加盖了两枚公章,法定代表人签了姓名。庭审中,被申请人认可,盖章行为是双方认可结算总价的行为。
2019年11月28日,案涉工程验收合格。《竣工验收报告》载明,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
【争议焦点】
被申请人辩称其主体性质为国有,案涉项目的建设资金也是国有资金,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也约定了结算审计,所以案涉工程款项支付前提应该是行政审计,而本案尚未完成行政审计,所以其认为目前支付条件不成就。
申请人认为,《施工合同》中关于审计的约定,并不明确,既未约定审计单位,也未约定审计形式,不能得出案涉工程应由审计局审计的结论。行政审计是对被申请人的行政监督,不影响双方之间的结算。双方在2019年7月已经就工程款达成结算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在2021年才提交审计,构成恶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视为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故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合同约定的“审计”的性质,本案应否以行政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
【裁决结果】
审计结论不能作为确定案涉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对被申请人的抗辩不予采纳,支持申请人关于支付工程款的仲裁请求。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中,即提出,“在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审核结论问题的答复》(〔2008〕民一他字第4号)称:“财政部门对财政投资的评定审核是国家对建设单位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及履行。但是,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审核结论应当作为结算的依据。”
但,根据《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规定》第二条与《重庆市建设项目审计办法》第二条规定,本案应该由审计局审计,并以审计结论作为项目结算和付款的依据。
此外,《审计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该法第四十六条还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给予处罚。”
【结语和建议】
行政审计的主要目的是对财政投资规模、资金使用情况、有无截流国家资金、有无任意扩大投资、是否存在贪腐问题等行为进行审查监督,而工程款结算是合同双方对已完工程量及造价进行协商确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两者在性质、范围、效力、主客体等多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审核结论问题的答复》(〔2008〕民一他字第4号)称:“财政部门对财政投资的评定审核是国家对建设单位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及履行。但是,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审核结论应当作为结算的依据。”参照该答复,只有在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财政投资审核结论(即行政审计)作为结算的依据。
对“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理解,一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严格把握:一是合同必须明确约定为行政审计,不能因案涉工程属于依法应当行政审计的工程,且合同约定了应当进行审计,就推定合同约定的审计系行政审计。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中,即提出,“在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的方式”。本案中,《施工合同》第12.4.1条第4款约定,完成结算审计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审定金额的97%,并未明确该审计系行政审计。二是必须有以审计结论作为确定工程价款依据的明确意思表示。如发、承包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程结算价款由行政机关依法审计”,仅表明双方愿意接受行政机关的审计,但并不等于同意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也不能依合同双方有配合审计机关监督检查的行为——如向行政审计机关提交材料、配合审计的现场勘查——就推定双方同意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就此,《施工合同》第12.4.1条第4款的约定尚未达到清晰无误的要求,存在他种解释的空间。此外,2020年2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序推动企业开复工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0〕5号)。《通知》第(七)条称,“规范工程价款结算,政府和国有投资工程不得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建设单位不得以未完成决算审计为由,拒绝或拖延办理工程结算和工程款支付。”且案涉工程在2019年5月竣工,7月达成结算,迄今未见审计结论。综合上述因素,仲裁庭认为,本案不应以审计局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建设工程实践中,凡涉及到使用国有建设资金,发包人通常都会与承包人在施工合同中约定“甲方应付工程价款的数额最终以审计机关(或甲方上级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为准”,即使双方未在合同中作此约定,甲方负责人出于行政责任的考虑,最终也会在工程款结算之前等待审计结果,致使承包人产生不确定的风险。在审计形式上,除审计机关审计之外,双方还可能会约定财政审计、上级审计、审计机关委托社会中介审计等等。但不论约定哪种审计方式,一旦审计结果与双方结算的数额差距过大,就可能诉诸法律,如何确认工程款必然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处理政府投资项目的行政管理和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问题。
民事合同以当事人自治为原则,以行政干预为例外,除非双方当事人对行政介入均有预期并作了明确约定,否则不应介入。对承包人而言,能否接受以“以行政审计为依据结算工程款”这一条款,应充分考虑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力争排除适用审计的不利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