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8年5月2日,被申请人(自然人叶A)和(自然人杜B)与案外人(自然人吴C)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8年第0501号的《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叶A和杜B共同向吴C借款32万元。叶A和杜B指定自然人刘D在交通银行香港路支行所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借款期限为360天,从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4月27日止。借款利息自款项到账之日起开始计算,利率每月按借款本金的1.1%计算。利息每1个月支付一次。借款期限届满后,叶A和杜B若不能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的,其违约部分的借款,从超出还款期限的次日起, 吴C有权按月利率3%收取利息,并按违约部分借款的0.5‰每日计算违约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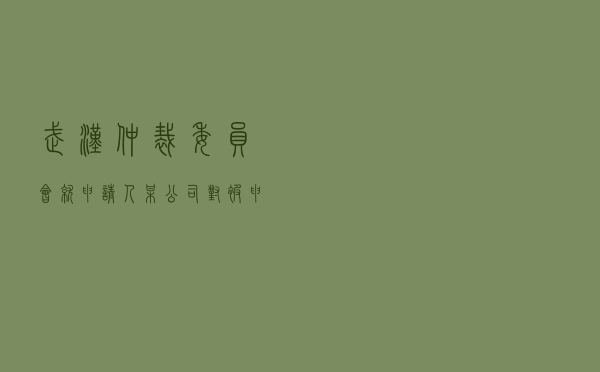
同日,叶A与吴C还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为了担保债权人吴C与债务人叶A和杜B所签订的编号为2018年第0501号《借款合同》的履行,抵押人叶A以其位于XXX一套建筑面积为67.09平方米的房屋作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32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其他应付的费用。
与此同时,抵押人叶A向抵押权人吴C出具了一份《承诺函》。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借款人叶A和杜B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出借人吴C借款32万元整,期限360天,从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4月27日,具体以实际放款日期为准。抵押人叶A自愿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1、抵押房地产坐落于XXX处,面积为67.09m2。
2、本人自愿将上述房产抵押给你方,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将房产证、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交于你方保管,同时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3、该房地产的现状为本人自用,具体用途为居住,本人保证维持该房地产的现状,如需改变房地产的现状,需提前一个月书面征得你方同意,并不得对你方的抵押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4、在你方主张实现抵押权的情况下,本人保证在15个工作日内腾退该房地产,并有义务自己解决因房地产腾退另寻住所的问题,费用由本人承担。
5、如借款人违约,你方有权选择向该笔债权债务有关的各方中的任意一方或者多方主张还款义务,本人放弃抗辩权,不以你方行使其他担保权利为条件。
2018年5月4日,某某市不动产登记局为上述房产抵押办理了登记手续,并出具了《不动产登记证明》。
2018年5月9日,出借人吴C向《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自然人刘D在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香港路支行所开立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32万元。
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叶A和杜B未能如约偿还借款本息。
2019年11月25日,出借人吴C与申请人某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出借人吴C将2018年第0501号《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某某公司。此后,某某公司分别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叶A和杜B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函》。
2020年11月2日,某某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提出的仲裁请求为:
1、裁决被申请人叶A和杜B共同向申请人某某公司支付借款合同所约定的本金32万元;
2、裁决被申请人叶A和杜B共同向申请人某某公司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42,080元(以本金32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9年4月23日起支付至付清为止,暂计算至2020年7月15日);
3、裁决被申请叶A以其所抵押的房屋价值为限,在第一、二项请求范围内向申请人某某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申请人有权就该房屋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范围内优先受偿;
4、裁决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叶A和杜B共同承担。
仲裁过程中,申请人某某公司向仲裁庭申请撤回了一组其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的证据。该组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叶A曾在某网络借款平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20万元。此后,该笔借款由某一融资担保公司予以代偿,代偿总额约为22万元。
根据申请人某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叶A出生于1951年,年龄70岁,其与杜B系母女关系。两人同住于同一居所,即上述所抵押的房产所在地。仲裁法律文书由叶A负责签收。但此后两人既未提出答辩,亦未到庭参加庭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所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仲裁庭认为,某某公司申请仲裁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明显有悖常理,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并且其所提交的核心证据——吴C向刘D转账32万元的付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吴C向叶A和杜B履行了出借资金的义务。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仲裁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3条、《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9条第(一)项的规定向申请人某某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对下列事项作出补充陈述并提供相关证据:
1、吴C向刘D转账支付32万元资金的来源;
2、刘D收到吴C转账32万元后的资金去向及用途;
3、刘D对32万元资金进行处分是否得到借款人叶A和杜B的授权;
4、某某公司受让吴C所转让的债权是否支付对价。
申请人某某公司收到上述《举证通知书》后,既未就上述事项作出补充陈述,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而是于2021年4月6日向仲裁庭提出撤回仲裁申请。
【争议焦点】
本案是否因“套路贷”而引发的虚假仲裁案?
所谓“套路贷”,是指行为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受害人签订借款协议并出借少量资金,然后通过肆意认定违约、更换出借主体、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资金转账痕迹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等公权力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所谓“虚假仲裁”,是指行为人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裁决结果】
2021年5月 日,武汉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书》,准许某某公司撤回仲裁申请。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2018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一条指出,“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
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的常见手法和步骤包括以下情形:
(1)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行为人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传,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诱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或抵押协议。
(2)制造资金转账痕迹等虚假给付事实。行为人按照虚高的借款协议金额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或他人账户,制造出已将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银行账户的流水痕迹,随后便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收回,被害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或者未完全取得借款协议和银行流水账单上所显示的资金。
(3)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行为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
(4)在被害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行为人往往借助诉讼、仲裁、公证等公权力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
从某某公司提交和撤回的证据来看,仲裁庭对本案是否系“套路贷”而引发的虚假仲裁案产生合理怀疑。
【结语和建议】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给仲裁机构的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
“套路贷”属于犯罪行为,借款本金和利息均不受法律保护。而民间借贷体现了双方意思自治,借款本金及一定幅度内的利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2020〕17号)第二次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双方所约定的年利率未超过24%的,或者在此之后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未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均受法律保护。
“套路贷”的实质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并具备知识型犯罪的特征,甚至有法律从业人员成为作案人的“军师”,给予其专业的“法律指导”,因此其隐蔽性强,并往往借助诉讼、仲裁、公证等公权力追索“债务”,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书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有的在实施“套路贷”诈骗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还可能构成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案中,仲裁庭对出借人所出借资金的来源、行为人刻意制造的银行转账凭证的资金流向、案外人对资金进行处分是否得到借款人的授权、受让债权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对“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进行甄别,从而让申请人知难而退,主动撤回仲裁申请,阻断了“套路贷”的进一步发展,维护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