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申请人A进出口公司常年为第一被申请人B食品公司(香港)提供代理进口、垫付进口冷冻货物之货款、税款及相关业务付汇款等业务。2017年3月,双方经协商签署了《欠款确认函》,确认第一被申请人截至《欠款确认函》签署之时,尚欠申请人融资、业务服务费的具体金额以及该等欠款的具体偿付方式及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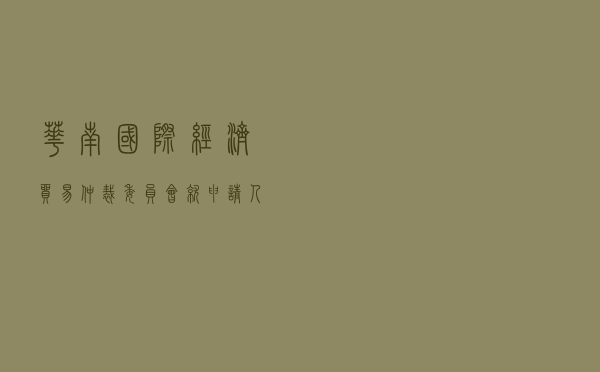
2017年11月,申请人、第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C某(第一被申请人董事,香港居民)共同签署《结算协议书》,确认截至《结算协议书》签署之日,第一被申请人尚欠申请人有关款项的具体金额为人民币1,176,604.54元,并约定了偿付方式及时间:第一被申请人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申请人现金不少于人民币500,000元;第一被申请人同意将仍存放于申请人处的货物继续销售,销售所得款用于归还欠款,汇入申请人账户。若第一被申请人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能销售,则同意申请人代为销售,销售所得款抵扣第一被申请人的欠款。自2018年1月1日起,第一被申请人同意在每月月底前以未还款金额为本金,按月息1.5%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利息。
此外,第二被申请人在《结算协议书》中承诺,当第一被申请人未履行付款义务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份《结算协议书》,第二被申请人分别在第一被申请人代表人处及担保人处签字捺印确认。但该《结算协议书》并未加盖第一被申请人公章。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公司资料可以判断,第二被申请人是第一被申请人的单一董事。
经申请人多次催促,第一、第二被申请人仍未付清前述款项,故申请人依据《结算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于2018年11月30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第一、第二被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人民币1,176,604.54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月息1.5%计算,利息暂计至申请仲裁之日为人民币194,139.77元),并由第一、第二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第一、第二被申请人未答辩。
【争议焦点】
2017年11月签订的《结算协议书》,在仅有第一被申请人单一董事签字,未加盖第一被申请人公章的情形下,是否能对第一被申请人产生约束力?
【裁决结果】
(一)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剩余款项人民币1,131,104.54元及利息(按人民币1,131,104.54元为基数,按月息1.5%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第二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前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第一、第二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人民币49,959元。
【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涉港澳地区的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配套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
因本案第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分别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有限公司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配套司法解释确定准据法。
(二)关于涉外合同,应尊重当事人约定法律适用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结算协议书》第9条约定,申请人与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共同约定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法律适用选择的约定不违反仲裁地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其效力应予确认,处理本案合同争议应当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
【案例评析】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结算协议书》的合同效力。在申请人提交的《欠款确认函》中,第一被申请人的代表人处,有第二被申请人的签字,且加盖了第一被申请人的印章。然而在《结算协议书》中,则仅有第二被申请人的签字及手印,没有第一被申请人的公章。本案中第二被申请人作为在香港设立的第一被申请人的唯一董事,是否有权代表第一被申请人签署合同,以及第一被申请人在签署相关合同时的形式(未加盖公章)是否符合要求,这些问题均属于“法人相关事项的法律适用”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上述问题应当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经查阅《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条例》第127条关于“公司签立文件”第(3)款规定:“公司亦可藉以下方式,签立文件——(a)(如属只有一名董事的公司)由该董事代表公司签署该文件”;第(5)款规定:“按照第(3)款签署的、在其中说明(不论措词如何)是由有关公司签立的文件具有效力,犹如该文件已藉盖上该公司的法团印章而签立一样。”
鉴于本案中第二被申请人为第一被申请人的单一董事,符合上述规定中关于董事代表公司签署文件的要求,同时,《结算协议书》第10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签字人不可撤销地保证已得到协议各方充分、合法的授权签署本合同”,符合《公司条例》第127条第(5)款规定的要求。
据此,仲裁庭认为,《结算协议书》虽未加盖第一被申请人的公章,但第二被申请人作为第一被申请人的唯一董事,代行第一被申请人权利,签署了该协议,且在《结算协议书》中对该授权签署亦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应视为第一被申请人签署了《结算协议书》,《结算协议书》是第一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第一被申请人有约束力。
综上,《结算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均进行了有效签署,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主体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相应的义务。
【结语和建议】
在涉外民事合同纠纷的审理中,有时不免须先对涉外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判断后(下称“先决问题”),才能继而判断涉外民事合同的效力。但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忽略对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判断,继而适用了错误的准据法解决先决问题。
在双方当事人均参加了庭审并充分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基于当事人的自认,仲裁庭可能并不需要有意识地或主动地对先决问题进行查明。但本案中,第一、第二被申请人均未积极应诉,申请人也仅提供了基础的被申请人主体信息。此时,仲裁庭发现了案涉协议中缺失了第一被申请人公章这一事实,产生了“仅授权代表签字的协议是否能够对境外公司产生约束力”的合理怀疑,则应当主动对这一问题进行查明,确认该问题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再以此为准绳找出问题的答案。而当解决了先决问题之后,才能根据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