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申请人张某从事皮鞋加工业务。被申请人李某某系成都某商贸公司聘任的运营部门的总经理,聘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为2018年4月1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2020年1月6日前工商登记信息上所载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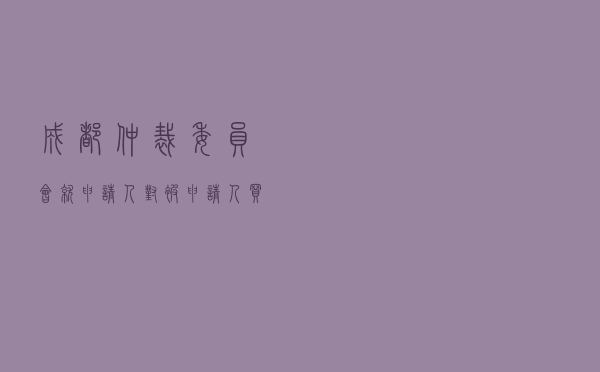
2020年1月4日,申请人(甲方)与被申请人(乙方)签订《对帐单》,约定 “一、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止,乙方尚欠甲方货款385429元。二、本对账单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三、双方若因该货款事宜发生纠纷,任何乙(一)方可向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简易程序)。”《对账单》落款处乙方李某某签字捺印并书写个人身份证号码。
庭审中,经仲裁庭询问,申请人陈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对账单》确认的款项,是在此期间不停的供货和结算,多次形成的欠款。此前的货款支付有现金和转账,转账是以刘某开户的银行卡转给申请人的。供货信息是申请人提供给李某某,日常的订单是李某某在负责。申请人请求的货款是基于和李某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刘某与申请人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是一笔供货关系,只是用刘某的卡在打钱。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签订《对帐单》后,一直拒不向申请人支付欠款,申请人经再三催告无效后,提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货款385429元及利息(略)。
被申请人辩称:我和申请人之间没有订立过任何订货合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账单》是我作为成都某商贸公司总经理所签,我个人和申请人没有任何生意上的资金往来,申请人找不到公司老板了,就根据我此前代表公司和申请人签订的《对账单》来找我。我是职业经理人,负责统筹公司的生意安排等,行使公司总经理的职权,但是我和物流方、供应商包括申请人之间没有任何生意来往,也没有向公司员工发放过任何工资。几年来申请人和公司之间存在上百万元的生意流水,但是我个人和申请人之间也没有任何资金往来。补充一点,公司也没有和申请人签订过买卖合同。
【争议焦点】
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裁决结果】
被申请人李某某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张某支付货款385429元及利息。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核心证据是《对账单》。搜寻相关适用法条和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与本案基本事实高度吻合,故仲裁庭以此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
本案核心是审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即确定《对账单》的清偿责任主体。
仲裁庭认为,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对帐行为是合同履行过程中或结束时对连续交易行为的清理。申请人以《对账单》主张被申请人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主体,被申请人抗辩其是履行职务行为,主张应由其所属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对帐单》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个人签署,被申请人在其上签字捺印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但并没有向相对方即申请人披露委托人或显示受托人外观证明,同时也没有证明事后成都某商贸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对被申请人的签字行为予以了追认的证据。依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申请人应对其职务行为的主张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被申请人庭审中提供了聘用合同、成都某商贸公司营业执照、王某的物流清单、订单、对帐表、公司内账等否定性抗辩证据,但前述证据中的物流清单、对帐表、公司内账等证据由于无法确认其证据“三性”,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而未被仲裁庭采信,无法证明该《对账单》的实际主体是申请人和成都某商贸公司或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故签署《对账单》的责任应当由行为人即被申请人承担,因此仲裁庭对被申请人的职务行为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仲裁庭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对帐单》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零星订货、阶段结算的交易方式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反的足以推翻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仲裁庭认定该《对帐单》所证明的买卖合同关系是真实的,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综上,被申请人应按照《对账单》的约定,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结语和建议】
社会经济生活中,尤其熟人社会圈,时常出现没有书面合同,以交易习惯、实际履行为特征的买卖关系,发生纠纷或争议后,一方仅出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债权债务凭证来主张权利,如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或许诺销售货物清单等,由于缺乏清晰的交易过程链条,如付款凭证、交付标的物凭证、所有权转让物证等,导致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模糊不清,相关权利义务不唯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特别强调,针对此种情况要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其中,方式和习惯要符合行业通常性、常理、人情、惯例;相关证据就是要证明交易发生而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客观事实,否则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混淆状态,达不到证明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查明事实,就应当予以认定争议双方买卖交易关系成立。
其次,当事人在债权债务设立中须谨慎作为,避免真实意思表达不准确或不完整。本案被申请人以个人名义和信用签署《对帐单》,表明双方结算货物买卖合同真意。从行为本身来看,不仅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也符合合同效力规则,且设定仲裁条款解决争议方式直接约束《对帐单》签署双方,并不涉及第三人。被申请人意图证明职务行为,须在《对帐单》中表明委托单位(人),或举示其他与签署行为有关联、能够证明履行职务的外观证据,否则只能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排除其他可能。据此,抗辩当事人必然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从另一角度看,当事人在签署债权债务文书时,须谨慎作为,避免真实意思表达不准确或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