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20年1月2日、7日,申请人A公司为投保人、被保险人,被申请人B公司为保险人,分别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子保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载明为涉案某半挂牵引车投保,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为352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1万元,均不计免赔,保险费合计16489.11元。特别约定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甲融资租赁公司,如赔付金额2万元以下,无需第一受益人授权,可直接赔付A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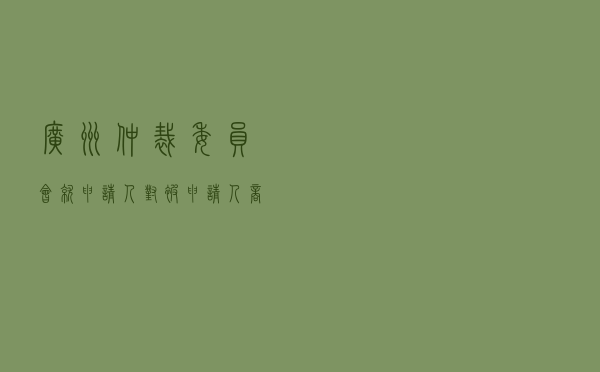
2020年1月17日,双方变更特别约定如下:1.删除原特别约定;2.增加特别约定为:本保单保险赔偿金第一请求权人为乙公司。双方及保险赔偿金第一请求权人同意当发生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险时,当赔款金额≤5万元,保险理赔金额可由A公司直接领取。当一次事故的保险赔款>5万元时,B公司须征得第一请求权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对A公司支付(第三者责任现的保险理赔除外);未经保险赔偿金第一请求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变更保险赔偿金第一请求权人,不得退保、减保或进行任何批改。
2020年3月2日,A公司司机杨某(具有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人员从业资格)驾驶涉案车辆在道路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及公路设施损坏。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杨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日,某公路事务中心出具《损坏路产处理记录表》,载明: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损坏公路路产,索赔金额为12002.8元。3月5日,某汽车救援公司开具发票载明:拖车费1320元、现场清理费100元、吊车费4000元、解锁费400元,合计5820元。
2020年5月19日,A公司委托某评估公司对涉案车辆受损维修费用进行价格评估,评估车损费用为308476元,A公司为此支付了评估费15424元。
另查明如下事宜:1.A公司提交乙公司出具的《车险赔款支付通知》载明乙公司同意将涉案车辆保险赔款318053.8元索赔至乙公司或乙公司指定的A公司账户;2.根据B公司委托,仲裁庭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车辆损失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2021年8月9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载明涉案车辆损失为300231元,鉴定费用为5000元。
现A公司提起仲裁请求要求B公司承担车辆损失费308476元、价格评估费15424元、施救费5820元。B公司则以A公司未获第一请求权人乙公司书面同意,认为其依约可不予赔付给A公司;同时对鉴定报告存在异议(认为仅对车辆换下的旧件进行勘察、未对修复后车辆进行查验,无法确认是否实际更换相关配件),要求重新鉴定,并认为A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施救费、事故损坏市政配套设施费用不合理。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A公司能否要求B公司直接向其赔付保险赔款?2.本案鉴定报告的效力如何?3.A公司主张的市政配套设施费、评估费、施救费应否支持?
【裁决结果】
仲裁庭经审查认定,首先,根据乙公司出具的《车险赔款支付通知》,乙公司已同意将涉案车辆保险赔款支付至A公司账户,故B公司可以将保险赔款向A公司支付。同时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六条的约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人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范围,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付,故A公司有权要求B公司支付保险赔款。
第二,关于鉴定报告问题。本案鉴定机构的产生符合法律和仲裁规则规定,鉴定程序合法有效。B公司在知悉现场勘查的是车辆旧件之时至鉴定报告出具之前,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亦未在现场勘查旧件之后提出要求对涉案车辆进行查验,而是在鉴定结论作出之后再提出异议,理据不足,并对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但考虑到涉案车辆部分配件是否更换对于保险的赔偿金额存在一定的影响,酌情对于鉴定报告中评估的车辆损失酌情下调百分之十五为255196元。
最后,A公司主张的市政配套设施费有相关《损坏路产处理记录表》等为证,予以支持;其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车辆车损进行评估作出的评估报告未被仲裁庭采信,故对其主张的评估费不予支持;施救费中,现场清理费属B公司未承包挂车上货物损失,解锁费非施救必要费用,对上述费用不予支持。拖车费与吊车费,由于A公司投保的是半挂牵引车,对挂车部分未投保,且其证据无法证明车头和挂车分别对应拖车费与吊车费,结合B公司认可部分拖车费与吊车费情况,认定施救费为2532元。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根据该规定,“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但是随着交易形式的不断发展,在某些财产保险合同中亦出现了“受益人”概念。本案中保险条款中即约定了“本保单保险赔偿金第一请求权人为乙公司”,B公司据此认为A公司不应直接向其索赔保险赔偿金,后由于乙公司出具了书面的《车险赔款支付通知》,同意将涉案车辆保险赔款索赔至其指定的A公司账户,B公司的该抗辩即不成立。但是,财产保险实务中由于“受益人”约定涉及何人有权领取保险金的重大利益,这一约定经常引发纠纷,裁判机构在“受益人”条款约定是否有效、“受益人”法律地位如何以及理赔权益的仲裁管辖等问题都存在争议,具有一定探讨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包括:……(七)鉴定意见……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也可以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保险纠纷属相对专业领域,对保险事故定损的专业判断,一般需要通过鉴定程序由专业人士提出鉴定意见,供裁判者参考。对于鉴定意见是否采纳,还是要看鉴定意见本身是否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案中,仲裁庭依当事人申请启动鉴定程序,对于鉴定机构最终作出的鉴定报告交由双方质证后,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鉴定意见进行分析,并最终认定对鉴定报告评估损失下调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对于应当准许重新鉴定申请的情形,第四十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方面,更加明确了重新鉴定应当符合一定的标准,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进行重新鉴定。本案中,B公司提起重新鉴定申请显然不符合上述四种情形,结合案件情况,仲裁庭未予支持;另一方面与旧规定相比,本次规定增加了因鉴定人本身问题需要重新鉴定情况下,鉴定人应退还鉴定费的后果,体现对于鉴定机构从事鉴定活动从严把关。
【结语和建议】
财产保险法律关系是财产保险商品交换活动中生成涉及保险人、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等多个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方面,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取得投保人保险费的同时是否须支付经济对价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事故损失的赔付在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并可量化计算的同时,也相对依赖于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导致财产保险中的鉴定活动相对常见。对此,裁判者与当事人均需明晰鉴定启动程序、鉴定活动要求等程序性事项,以使鉴定制度发挥更好的效果,有效推进案事实的查明。另一方面,随着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商事模式更新换代,许多财产保险合同中亦多出现对于受益人进行约定的情况,对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约定应当如何理解,也存在争议。
鉴定已日渐成为民事诉讼中常见活动,弥补裁判者在财产保险等专业问题上认知能力的不足,为裁判者审理财产保险案件提供了助力。对于财产保险的鉴定活动。新民事证据规定对鉴定规则进行了完善,具体表现在鉴定的启动、鉴定人行为规范、鉴定意见的主要内容等方面。首先,鉴定启动主要基于当事人申请以及裁判者依职权主动启动两种情况,而最终是否决定启动鉴定则需裁判者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判定。而当事人单方面委托鉴定形成的报告则属于书证的范畴,是否采纳属证据采信问题;再则,鉴定需履行严格程序要求,如鉴定期限等有严格限制(裁判机构出具的委托书中应载明鉴定事项、鉴定范围、鉴定目的和鉴定期限),鉴定人应严格履行其义务(鉴定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客观公正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应经过双方质证等;最后,重新鉴定应当符合一定的标准,裁判者对重新鉴定耽误的审限应当从严把握。
而对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约定效力的理解问题。有观点认为受益人仅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存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无受益人的概念,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不应得到支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财产保险受益人的指定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其关于保险金的请求在理据充分的情况下应予支持。建议当事人在作财产保险受益人约定时了解司法实践关于该约定的最新裁判观点,在协商一致情况下对“受益人”合同地位以及理赔权益作出事先约定,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同时也期盼随着司法实践深入,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等可以得到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