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本案申请人为某国有独资大型科创企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引入区块链高新研发技术,向第一被申请人(某香港科技公司)单独在广州设立的公司(第二被申请人)投资,并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增资协议》,约定申请人为第二被申请人增加注册资本1350万元,第一被申请人承诺第二被申请人应于2019年12月30日前实现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3500万元、于2020年12月30日前实现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7800万元、于2018年至2020年期间归属申请人利润累计不低于694万元,如果未达到上述标准则触发回购条款,第一被申请人应在收到申请人相关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现金以回购申请人所持有的股权。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实际缴纳出资额877.5万元。后由于经营状况不佳,第二被申请人2018年的营业收入为94339.62元,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1363707.52元,2018年5月至2020年期间可归属申请人的利润尚未达到694万元,申请人认为股权回购条件已经成就,为此提起仲裁。两被申请人确认未曾向申请人分红,但抗辩称,其经历了“新冠疫情”“通行证过期”和“国际环境巨变”等多重打击,因不可抗力导致《增资协议》的业绩承诺无法实现,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回购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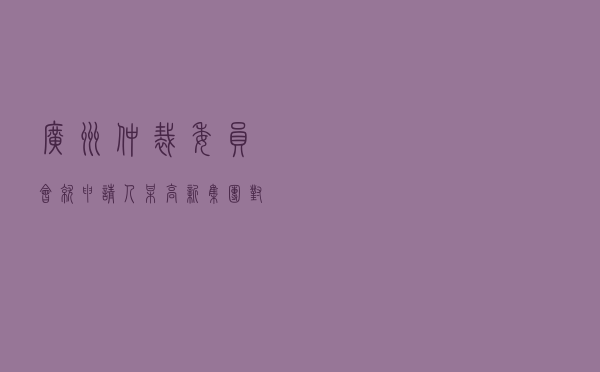
【争议焦点】
两被申请人所主张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等市场环境变化等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由?
【裁决结果】
仲裁庭经审查认定:
第一,本案第一被申请人为香港企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并未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仲裁庭认为,本案双方选择的争议解决机构为内地仲裁机构,《增资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位于广州市,本案应当适用内地法律。
第二,关于两被申请人主张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业绩严重受损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首先,第二被申请人的经营内容主要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该行业并非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的行业。其次,两被申请人均未举证证明疫情与第二被申请人或行业的业绩受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次,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时间为2020年初,而第二被申请人2018的营业收入为94339.62元,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1363707.52元,远低于《增资协议》约定的“第二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30日实现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3500万元人民币”的业绩要求,即第二被申请人未完成2019年的业绩承诺;且第二被申请人2018年、2019年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即使2020年未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第二被申请人业务运营正常,第二被申请人也难以在一年内向申请人分配高达694万元的利润。综上,仲裁庭认为,第二被申请人业绩情况与疫情无关,两被申请人关于因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业绩受影响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两被申请人主张的“世界经济危机”等市场环境变化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仲裁庭认为,不可抗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等;(2)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3)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虽然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难以预测,但这正属于商业风险,而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仲裁庭对于两被申请人关于因“世界经济危机”等市场环境变化的不可抗力问题导致业绩严重受损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两被申请人主张的应收账款未收回、无法贷款、法律纠纷等问题,均属于经营者可预见且应当预见的正常商业风险,并非不可抗力事件,两被申请人均不能因此免责。
综上,两被申请人均未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第二被申请
人业绩受损事实进行举证,因此仲裁庭对于两被申请人适用不可抗力免责的主张不予支持。《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股权的条件已经满足,第一被申请人应当按照《增资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支付股权回购款。
【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由于不可抗力具有不受当事人意志支配的特点,因而在各国法律中,一般都作为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我国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最早见于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第107条、第153条中,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民法典》中基本延续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与大陆法国家民法典中,将不可抗力作为免除民事责任情形的规定相一致。此外,《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项还规定了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可以作为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因此,一旦出现不可抗力,债务人所能获得的不仅仅是合同不能履行的免责抗辩,还包括合同解除请求权。
关于不可抗力的认定标准,理论上历来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凡属于基于外来因素而发生的、当事人以最大谨慎和最大努力仍不能防止的事件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从2020年初开始,在我国全国范围内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COVID-19”。从法律上分析可知,新冠肺炎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异常事件、一种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疫情,不仅当事人不能预见,甚至连具有广博医学知识的医学专家也未必能预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此前也就新冠肺炎疫情给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回应道:“当前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是指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和给当事人造成的履行困难情况,确定应当免除违约方的部分责任,或者全部责任,而不是一概全部免责。同时,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需要承担以下两项义务:第一,通知义务。即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让对方当事人及时了解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避免造成损失,或者尽量减少损失。第二,提供证明义务,证明可以是由公证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可以证明不可抗力发生的单位出具的书面材料,也可以是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有关不可抗力发生情况的报道材料。
【案例评析】
本案系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之间发生的增资协议纠纷。案件发生在广州市积极引入境外高新科技公司的背景下,通过内地企业对科技公司进行投融资,鼓励科技研发,推动广州市高新技术的发展,增强广州市科创企业的创新能力,为科技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后疫情时代,多数企业经营不善均会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由作为违约抗辩,实践中,应结合案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正义。本案仲裁庭通过充分的说理论述,有效化解两地企业之间因适用法律、政策规定及行业发展情况的不一致而引起对合同义务的理解认知不清的困境,体现了广州仲裁委紧跟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策略,充分发挥仲裁的功能与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间的发展提供和谐、合规的法治环境。
【结语和建议】
疫情的发生在人们的意料之外,而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市场主体都希望援引不可抗力制度来减轻自身的损失,但对于不可抗力的运用不能过于乐观,而是应该结合自身实际谨慎判断。一方面,《民法典》明确不可抗力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一般情形,适用时还需考察法律是否“另有规定”;另一方面,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不可抗力事件的存在,不必然导致免责。不可抗力对于责任免除的影响,关键在于其是否直接使得合同履行成为不可能,同时兼顾不可抗力在违约损失中的参与度等因素,综合考量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当事人之间约定以及疫情影响程度等因素,具体个案是否适用不可抗力免责,需结合个体情况而定。
本案《增资协议》本质上属于“对赌协议”,其实质是对商业经营中资本价值风险判断的合意行为,当事人在签约时理应能够预见到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商业风险及法律风险。所以,在此类协议中想要援引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免责事由的证明标准较高。《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的通知》第14条明确: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合理分配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因此,当事人想要证明疫情导致其业绩严重受损而阻却“对赌协议”相关业绩补偿条款的履行,不仅需要证明其属于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严重影响的行业,还需要证明疫情与其行业业绩的受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