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申请人称:2019年1月申请人购买被申请人开发的商品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登记局办理了备案,合同约定申请人购买被申请人商务办公楼,总价款6100万元。申请人应当在2019年10月前支付房屋全部款项,被申请人应在2019年12月底前向申请人交付该商品房。2019年10月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购房款6100万元,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购房款收款收据,由于被申请人未能按约交付房屋,双方一致确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460万元,后双方协商,将违约金调至720万元。2020年4月,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确认,申请人已经支付了全部房款,被申请人严重违约,被申请人应于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房屋交付给申请人,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产生的相关律师费。后被申请人未交付房屋,申请人请求:一、被申请人立即交付房屋(房屋地址为XXXX);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720万元;三、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120万元;四、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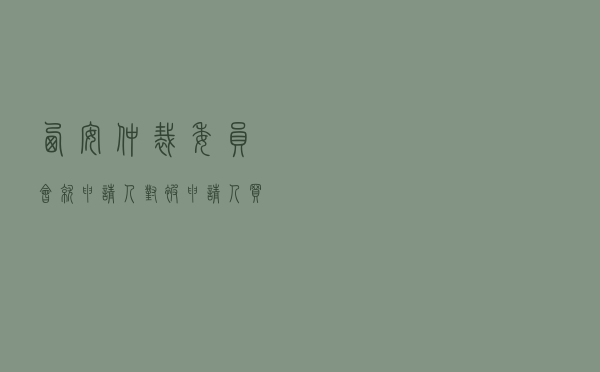
被申请人辩称:一、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纠纷,双方没有发生买卖关系。2019年1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2020年4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通过买卖形式实现债权担保,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房屋让与担保,故“交付房屋”的约定无效。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商品房买卖的意思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上述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三、双方签订的《房产回购协议》中“如被申请人未按期支付回购款即自动放弃回购权利,应配合申请人将房屋办理至申请人名下”违反法律禁止流押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仲裁庭审理查明:2019年1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还签订了《房产回购协议》。2019年10月,申请人支付购房款6100万元,被申请人开具了购房款收据。由于被申请人未能如期交房,2020年4月,双方另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对上述一系列合同,被申请人认为合同目的并非房屋买卖,而是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实现债权的担保。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所载内容,涉案房屋共计三层,为整理设计,但合同中申请人购买的层数为2,但面积为整个三层的面积。另,该合同购买资金属国有资金,需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本案中并无相应批准文件。
【争议焦点】
本案所涉合同性质?
【裁决结果】
基于上述意见,裁决如下: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无效。
二、申请人协助被申请人在裁决生效后30日内办理合同备案注销手续。
三、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四、本案仲裁费XXXX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已由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在履行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时一并给付申请人。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本案所涉合同性质?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基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是否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申请人主张双方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申请人抗辩双方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关系。首先,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备案证明、收款收据等证据,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该《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及履行的真实性。其次,被申请人主张本案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法律关系,对该主张,被申请人提供《房屋回购协议》、收款收据非公司销售所出具证据等内容。
本案中,涉案房屋坐落于某市,该房屋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市场价17000元,但双方约定的价格为7000元,远低于市场价。另外,涉案房屋为一整栋,但本案中申请人仅购买其中一层,但合同中记载的面积为整栋房屋的面积。同时,在房屋买卖交易中,往往习惯明确约定房屋交付时间、违约金具体计算方式,本案中并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交付时间,仅约定为“某月”交付。结合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收条内容、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足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无效。
【结语和建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及《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第33条的规定,当合同的名称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类型和案由,并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企业间署名为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的,应审慎定性合同的性质。如根据各项证据证明企业间签署的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的,应按照借贷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而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判断核心在于审查该行为是否属于《商业银行法》所明确禁止的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行为。如出借企业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损害金融秩序,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