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4年至2015年间,李某在经营管理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过程中,未经某公司许可,指使员工对某公司的《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软件V3.1》进行修改,冒充其代理商将软件销售给某医院,以本公司名义销售给另五家医院,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428.12万元。并将修改后的软件进行了著作权登记,于2015年4月、7月取得著作权登记证书。后被某公司发现,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给上述各医院的软件与某公司的《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软件V3.1》存在复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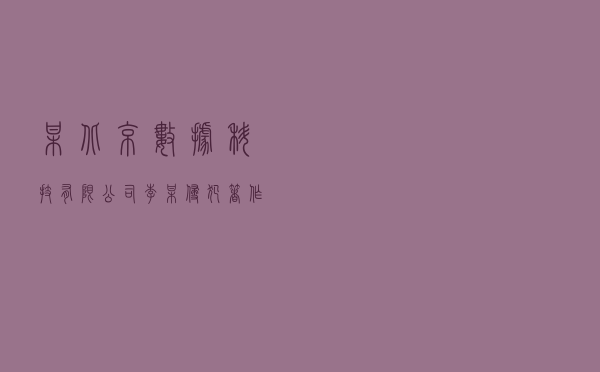
【调查与处理】
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李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4月2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李某侵犯著作权罪,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6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以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分析】
本案在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围绕案件事实和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需要对被告单位及被侵权单位的著作权哪个在先、两个软件中“相同的核心源代码”能否认定软件属于“实质性相同”、部分复制“实质性相同”软件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复制”三个问题进行着重分析。
1.被告单位及被侵权单位均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如何认定哪个著作权在先。
著作权登记是形式审查,有证书不证明不会侵权,登记时间早的也不一定表示作品完成在先。因此,要通过在案的其他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哪方的著作权在先。本案中,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2011年取得软件的著作权证书,被告人李某2013至2014年在该公司工作时,软件已经广泛销售、使用,并在业内取得好评。而被告单位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是李某在某公司离职后,取得著作权证书的日期更晚。因此综合判断,某公司是著作权在先。
2.在两个软件中“相同的核心源代码”是可以公开使用的开源代码的情况下,能否认定软件属于“实质性相同”。
本案中,销售给六家医院的软件并不完全相同,被告单位根据开发进程及客户要求,对某公司的软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因此与原版软件相比,相同的源代码数量不完全一致。
例如:某公司的软件与某医院硬盘中软件的同异性鉴定报告
①鉴材一源程序及数据库文件有效,可编译运行。
②鉴材一、鉴材二程序目录结构实质性相同。
③鉴材一、鉴材二源程序核心代码“*.jar”、“*.js”文件比对情况:
“*.jar”文件:鉴材一有68个,鉴材二有71个,比对有65个相同或构成实质性相同,分别占鉴材一比例为96%、占鉴材二比例为92%。
“*.js”文件:鉴材一有349个,鉴材二有487个,比对有228个相同或构成实质性相同,分别占鉴材一比例为65%,占鉴材二比例为47%。
结论:鉴材一与鉴材二之间存在复制关系。
被告单位始终对鉴定意见中的结论有异议,称鉴定相同的“65个‘*.jar’文件”是公开的开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下载使用;且多个数据库表相同或实质性相同是因为涉案软件子模块报告财务模块等,绝大部分都是国家规定的表格格式。否定软件之间存在复制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信专业鉴定机构的结论,认定软件是否实质性相似是本案的关键。对此,承办人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咨询了软件行业的专业人士,了解了行业的专业知识;并及时与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沟通,针对案件的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咨询,获取了专家的专业性意见。
鉴定机构的专业性意见是:即使被鉴定相同的软件是公开的开源代码,但是免费使用的公开开源代码很多,两个软件却均使用了相同的65个*.Jar文件,*.js文件也有部分实质性相同,再者,两个软件的目录结构也是实质性相同的,这种情况下,两个软件还是存在复制关系。因此该公司的辩解并不能否定两个软件存在复制关系。
结合实质性相似原则、接触原则以及专业机构的意见,驳斥了被告单位的辩解,最终认定软件实质性相似。
3.部分复制“实质性相同”软件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复制”。
本案中,某公司及李某未经许可,将某公司的计算机软件修改后复制发行的行为,属于“部分复制”实质性相同的计算机程序文件。这种行为符合刑法意义上的“复制发行”:
首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在刑法没有明确界定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中“复制发行”含义的情况下,将“部分复制”纳入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范围具有一定的法律根据。
其次,某公司并没有对某公司的软件作实质性的改进,是在某公司软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便更名为新软件,该新软件所包含的智力创造仍是某公司独自的劳动成果,不具有某一方面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并不是新的作品。
综合分析,本案系由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非法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某公司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引起,李某具有在某公司从事软件工作的经历,且作为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该起行为负有责任,鉴于李某没有前科劣迹,且能当庭认罪、悔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某(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专业性较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对案件办理人员要求较高。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在司法实践中推广以案释法,扩大以案释法工作影响力。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庭审前加强对被告单位的释法说理,庭审后注意总结经验做法,使案件审判过程与普法教育过程有机融合,取得良好效果。二是推进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在该案普法宣传过程中,注重弘扬职业道德,有针对性地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三是深化“法律六进”主题活动。大兴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案件办理过程,加强对涉案企业法律宣讲工作,切实增强了企业学法用法能力、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