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2年7月17日3时15分许,受雇于某建材公司的货车司机汪某驾驶超载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李某驾驶的重型普通货车右后侧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汪某左股骨干骨折、右踝骨骨折等多处损伤。在汪某住院期间,某建材公司法律顾问——天津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某与某建材公司经理之妻郑某持汪某签字捺印的授权委托书,以汪某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赔偿经济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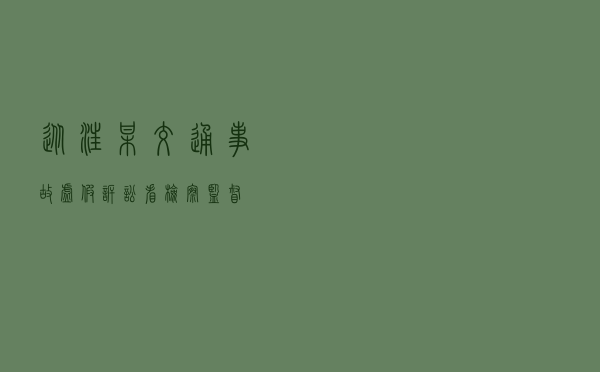
2012年12月15日,许某、郑某以汪某名义与李某在法庭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内容为:李某一次性给付汪某医疗费4万元,汪某放弃后续治疗费诉权并永久息诉。后许某、郑某二人以汪某名义领取了赔偿款。
【调查与处理】
(一)调查过程
本案由检察院举报中心移送。举报人汪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被告知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汪某不能向法院提起该诉讼。经仔细询问并查阅原始案卷得知,由于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已由律师许某和郑某代为起诉,故案件已经审理终结并执行完毕,执行款已被许、郑二人领走。无奈之下,汪某向检察机关举报。
案件受理后,经过调查发现本案疑点有二:1.案件审判卷宗中只有一份授权委托书上有汪某的签名和指印,其他文件中汪某签名系律师代签,不排除签名被伪造的可能;2.汪某本人及家属在整个诉讼过程均未参加,甚至在领取赔偿款时都是由律师代理,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承办人在第一时间提取了汪某十个手指的全部指纹,并让其现场签名。经与审判卷宗中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和指纹比对,发现存在明显差异,由此认定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指印均系伪造。随后承办人取得汪某之妻的证言,证实汪某事发后一直在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某建材公司曾将汪某身份证件拿走用于处理事故,但未曾委托他人代替汪某起诉,该证言与汪某所述相互印证。在随后对律师许某的调查中,许某承认自己未按照规定办理委托手续,赔偿款已被某建材公司郑某领走。
由此,可以判断法院的审判活动存在如下问题:1.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未尽严格审查义务;2.违反了调解合法、自愿原则;3.未按照法律规定发放执行款。律师许某及某建材公司经理之妻郑某伪造授权委托书,冒用他人名义提起诉讼的行为明显违反法律,妨害了正常的诉讼秩序。
(二)监督意见
针对法院审判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于2013年3月29日以案件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理由如下:1.审判人员未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许某、郑某利用伪造的授权委托书提起民事诉讼,侵害了汪某本人的诉讼权利;2.汪某本人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之诉,也没有与李某达成调解之意愿,许某、郑某与李某达成的调解协议并非汪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应属无效。
针对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直接将赔偿款发放给代理人致使本应属于汪某的赔偿款项被他人领走,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妥善处理本案赔偿款并进一步规范该执行款的发放。
针对律师许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检察机关于2013年4月3日向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狠抓律师执业纪律、规范律师代理行为,对涉案律师许某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罚。
(三)监督结果
法院收到建议后,于2013年5月7日召开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讨论。经讨论决定,撤销原调解书、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并表示今后汲取教训,严格审查委托代理手续,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2013年8月8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1.撤销检察机关原民事调解书;2.驳回许某以汪某名义对李某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起诉。
针对案件执行情况,法院在第一时间对已经执行完毕的赔偿款进行了执行回转;并针对审判规范和执行活动进行专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严格规范立案审查、开庭审理、文书送达、款物发放四个环节的委托代理手续,确保代理意愿和代理权限的真实性。
针对律师的无权代理行为,司法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对案件情况进行核查,最终认定律师许某的诉讼代理行为存在过错,对其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又将案件情况和司法局的处罚决定反映给天津市律师协会,该协会认为律师许某在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私自进行代理的行为,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给予许某停业、行业内谴责的处分。
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许某、郑某二人存在妨害诉讼活动的犯罪行为,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公安局宝坻分局立即进行立案侦查,并对二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法律分析】
本案最终是以虚假诉讼案件进行处理。传统意义上的虚假诉讼是指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以伪造、变造的虚假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在诉讼过程中采取隐瞒真相、虚假陈述等非法手段进行欺诈,致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进而公然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诉讼行为。虚假诉讼的案件通常具有以下特点:1.多发生在与财产利益相关的案件中;2.伪造的证据通常为直接证据,且证据单一,缺乏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3.以调解形式结案的较为普遍,且此类案件极易达成调解。
虚假诉讼之“虚假”表现为:1.诉讼主体虚假,即作为原告或被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事实上不存在或者已经丧失主体资格;2.案件基本事实虚假,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借助”法院的判决侵犯对方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3.关键证据虚假,当事人通过伪造案件关键证据,造成错误裁判。
本案与传统意义上的虚假诉讼有所区别,本案系由无关人员冒名提起诉讼,其表现形式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虚假。本案中,许某、郑某二人持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以汪某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导致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案件从起诉到调解,均不是汪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中的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调解自愿、合法原则。
从另一种角度评析,本案许某、郑某二人以他人名义提起诉讼的行为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的合法财产性利益;行为之性质是对正常诉讼秩序的扰乱和妨害。许某作为执业律师而有意伪造授权文书,其主观意图表现更为明确。案件以法院审理活动审查不够严密而引发,但导致的后果却是审理、执行的系列错误,直接致使真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影响了司法公正与审判权威。
【典型意义】
本案以当事人向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最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司法公正。本案对法院审判活动、执行活动、律师代理活动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都具有典型意义:1.对法院审判而言,本案提示了新型虚假诉讼行为的存在,给予了法院审判更加严格的审查义务。同时针对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以调解结案的案件给予更多的风险警示;2.对法院执行活动而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发放执行款项,严格审查领取人的主体资格成为执行重点;3.对律师代理活动而言,本案既是对律师行业的警示,也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活动提供借鉴;4.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而言,多联合的监督行为将更有利于检察监督效果的实现。本案中,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检察建议、调查核实等监督方式和手段,实现了监督错误调解书、规范诉讼行为、查办违法犯罪的综合效果,也为建立防范、打击虚假诉讼的长效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彰显了司法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
本案的正确处理亦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优秀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例选》选编为精品案例,并多次被《检察日报》宣传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