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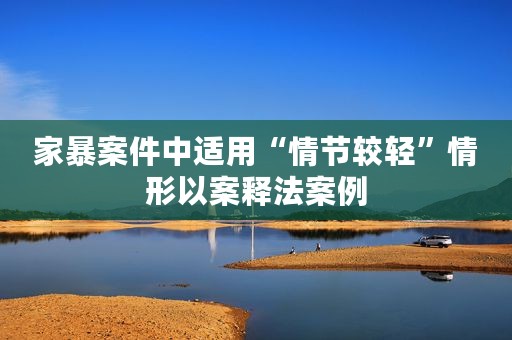
被告人张某及家人经常遭到其子张某生打骂。2008年2月20日22时许,张某因张某生好吃懒做对其进行了训斥,张某生辱骂并欲殴打张某,张某见状从外屋东北角拿一把镐头回屋击打张某生头部一下,将其打倒在地,后张某又在自家院内东侧拿一根绳子套在张某生颈部将其拖至屋外,又用镐头击打张某生头部数下,致张某生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场死亡。案后,张某委托他人报案,公安人员赶到张某家中将其带走。
【调查与处理】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致一人死亡。鉴于张某系因其本人及家人长期遭受被害人张某生暴力虐待而杀人,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在审理期间又能认罪、悔罪,对其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故依法可对其适用缓刑。根据张某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律分析】
本案的法律分析重点在于对因长期受虐而实施手段残忍的杀人行为能否适用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情形。
案件审理期间,张某的妻子、女儿向法院出具了书面材料,同时张某所在村的村委会及全体村民向法院出具了联名信,证实张某为人忠厚、老实,家庭特别困难,张某夫妇体弱多病,大儿子张某力患有精神疾病,至今未婚,两个女儿因害怕张某生殴打多年不敢回家,张某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张某生游手好闲、无恶不作,曾因打架被劳教,非但不思悔改,还经常酒后滋事,打骂家人,张某夫妇及张某力经常被张大生殴打,还扬言早晚把家人杀掉。张某生经常在外打架斗殴,没钱就向家人索要,如果不给就非打即骂。张某生将家里一年卖玉米的收入9000元全部拿走,又向他姐姐威逼2000元,如果不给就要杀全家,冬天时还向父母的炕被里倒凉水,不让他们睡觉。张某生劣迹斑斑,却将自己未婚原因归罪于父母没给他钱成家,于是变本加厉虐待父母和家人。承办人到张某所在村进行了实地走访,据村民反映,张某家人出具的书面材料及全体村民联名信内容完全属实,具有减轻处罚情节。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该条中的“情节较轻”如何理解和认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无具体、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将以下较为常见情形视为“情节较轻”:(1)防卫过当杀人,指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而故意将不法侵害者杀死的情形;(2)义愤杀人,是指行为人或其近亲属受被害人的虐待、侮辱或者迫害,因不能忍受,为摆脱该情形而故意实施的杀人行为;(3)激情杀人,指本无杀人的故意,因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而失去理智,当场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三种情形有一个共同点,即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有严重过错。具体而言,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对诱发被告人的犯意、激发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结合到本案,受虐杀子、大义灭亲的犯罪行为,从杀人原因和审判的法律、社会效果两方面分析,应当认定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该类行为系义愤杀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情形。理由如下:
(一)杀人原因分析。本案中,张某虽然杀人手段残忍,但却源于长期受到张某生暴力虐待所致。张某生虐待家庭成员由来已久,而家庭成员对此却默默忍受,虽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应为该家庭实际情况所致。据了解,张某夫妇的大儿子患有精神疾病,至今未婚,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张某生是家中的小儿子,也是整个家庭传承的唯一希望,老人本着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对张大生过于溺爱,姑息迁就,而张某生非但没有理解家人的良苦用心,却以虐待、迫害等方式加以对待。在长期遭受暴力及处于恐慌的过程中,张某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精神上的钳制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一旦爆发就容易走极端,于是在张某生再次欲对张某实施暴力行为时,张某丧失理智而实施杀人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因长期受虐杀子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
(二)从刑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分析。受虐杀子的行为量刑时,按照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对于遏制家庭暴力的滋生蔓延有积极的意义。将受虐杀子的行为认定为情节较轻,必然会使施暴者有所收敛,更加理智的去权衡自身行为后果的利弊,起到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传统的伦理道德告诉我们,虎毒不食子,父母是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的,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相比其他家庭成员要更加深厚,因此受虐杀子相比受虐杀夫或者发生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杀人行为就更加值得同情。张大生不仅在家庭内部实施暴力行为,而且危害乡里,对当地群众的人身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这在进一步加深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被告人行为的可谴责性。该类犯罪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犯罪,主观恶性比一般故意杀人行为要小得多,而且张某年届70岁,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性,再犯的可能性极小,严惩这样的人,对社会、家庭及子女都是弊大于利。将该情形认定为情节较轻,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顺应了刑罚“轻缓化”和“人道化”的发展趋势。
(三)量刑适当考虑民意。虽然民意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在量刑时应考虑对被告人有利的民意,综合其他因素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典型意义】
刑事法律负有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利益的义务,法律在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前提下,也不应忽略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当被害人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章制度,在道义上或法律上具有可谴责性和可归责性,且该行为是诱发被告人产生犯罪动机或者使犯罪动机外化最主要的因素时,就应当认定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在该情形下,对被告人就应考虑按照“情节较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