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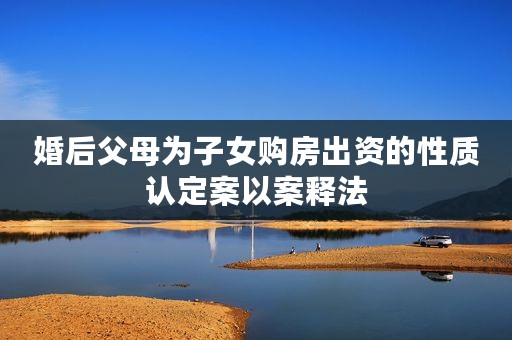
谢某与迟某经双方父母介绍认识,俩人迅速坠入爱河并于2010年4月登记结婚。刚开始迟某母亲王某对儿媳妇非常满意。希望子女能有个安居场所、也考虑到儿子迟某没有工作和积蓄,结婚时婆婆王某大方承诺会给二人购买婚房。于2010年10月全款购买房产,房款由王某支付,婚后登记在小俩口名下。后来夫妻感情逐渐破裂,2020年5月迟某向法院起诉离婚。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感情未得到有效修复,2021年迟某再次起诉谢某离婚。与此同时,婆婆王某将儿子迟某与儿媳谢某共同诉至法院,诉称迟某为购买房屋和车位向其借款178万元尚未偿还,要求谢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某为了证明借贷事实,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及有儿子迟某一人签字的借条作为证据。说好的“给买”婚房,谢某也当然以为婆家的出资属于婚后对自己和丈夫的赠与。而如今一方面被丈夫起诉离婚,另一方面被婆婆起诉偿还巨额债务,双重打击让谢某不知所措。
【调查与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主张出借人的原告系被告迟某的母亲,系被告谢某的婆婆。被告迟某于2020年5月向法院起诉与被告谢某离婚,后经判决不准离婚。现迟某又在法院起诉与被告谢某离婚,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基于该情形,对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应当从严审查。《民间借贷新规》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条上只有被告迟某的签字确认,没有被告谢某的签字确认,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谢某之间有借款的合意。原告虽然出示了借条,但是否是原告出资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有待考量,是否是真实的借贷关系也有待考量。第一,从借条的落款时间来看,系迟某与谢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迟某与谢某有借贷的合意,迟某理应要求谢某在借条上签名并让谢某知晓,但该借条仅有迟某的个人签名。第二,迟某从结婚开始至今没有工作,不具备长期的还款能力。第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答“当时我想如果他俩能给我养老送终,我不一定非要这个钱,现在因为他俩闹离婚,所以我现在主张还款”,可见其没有明确的借贷意思表示。综上三点,不排除原告为稀释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在事后虚构借贷关系而签署的可能性。如若只依据借条就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那先前成立赠与关系,事后签署借条就成立借贷关系,会使法律关系认定恣意泛滥。故仅凭借条并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因此原告基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也不成立。所以在原告对于借款关系举证不能以及原告出资行为发生在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原告的出资应视为对被告迟某与谢某双方的赠与,该赠与亦与我国婚嫁习俗相符(出资为当时的儿子儿媳购买婚房更切合实际)。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所有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案涉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上诉人并非将案涉款项直接交付给二被上诉人,而是直接转账给房屋及车辆的出卖人。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只有被上诉人迟某的签字,而无被上诉人谢某的签字。被上诉人迟某自认在借款当时以及事后均未告知谢某向上诉人借款事宜。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迟某为母子关系,被上诉人迟某以及谢某正在进行离婚诉讼,上诉人自认在本案前未向被上诉人谢某主张过权利以及在一审时关于“当时我想如果他俩能给我养老送终,我不一定非要这个钱,现在因为他俩闹离婚,所以我现在主张还款”的陈述,仅凭借条,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在款项发生时即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法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王某的出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否为借贷行为。
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但司法实践中,在适用该条文时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一些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父母出资意思不明的情况下,从社会的基本常理出发,应当推定出资属于赠与。而一些法院则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适用于父母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而非对父母出资款性质进行的认定。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父母出资款项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父母对子女购房的临时性资金帮助,当父母向子女主张返还购房款时,子女应当归还。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根据该条,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按照受赠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但《民法典》背景下再理解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应当准确把握立法意图。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一审法院在父母一方主张为借款的情况下,使其承担证明责任。在王某对借贷关系举证不能的情况下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这也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一致。
【典型意义】
父母在子女感情破裂闹离婚时,为了保住自己投入的积蓄,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夫妻还款的情况十分常见。这类案件发生于亲属之间,基本没有书面的协议可以清晰的界定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只能根据双方陈述,查清借款背景、出资金额、父母经济能力、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等来推断出资当时的真实意图。
父母的财产权益当然要保护,但要讲基本原则和诚信。对于那些出资当时就向子女及其配偶明示是借贷的情况我们应予以尊重和保护。但实践中很多家庭的父母明显引导子女的配偶让其认为父母的出资是赠与,以此来促成子女的姻缘,例如很多儿媳一方正因为男方出资赠与才最终决定婚嫁,有时因为考虑婆家出资购房付出较多,女方承担一切装修及办婚礼等费用。若干年后当子女与其配偶闹离婚时,一方父母立即与自己的子女串通声称出资行为是借贷而非赠与,以此达到稀释另一方财产的目的,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不应该被提倡。
本案判决虽适用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但也符合民法典的理念。鉴于父母与子女及其配偶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当子女确因购房需要向父母借款时,属于向外巨额举债,配偶当然有知情权,子女应当告知其配偶,此时父母也应当尽谨慎注意义务,明确告知子女的配偶该出资是借款的事实,让夫妻双方均在借条上签字,这也有利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在父母出资是赠与还是借贷这个问题上,有些判决真的没规则可循,有时为了平衡利益、照顾出资方,而对诚信原则熟视无睹。实践中,很多类似的案子,法官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都不难看明白,父母在小俩口结婚购房时出资意图明显是赠与而非借贷,但大家还是要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将“借贷”或“赠与”的论述进行到底,试图推翻既定的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认为这没错:凭什么媳妇或女婿结婚不久,就要分到父母大部分或者一生积蓄?所以,为了保障父母利益,绝不能让子女配偶得益,即便出资时的意图是赠与,也应将父母出资视为借款,让子女配偶偿还,保护父母这些弱势群体才是“正义”所在。我们明白子女闹离婚,媳妇或女婿要分到房产,损害了父母的利益,父母心有不甘。但绝不能为了保护所谓“弱势”群体利益就背弃诚信原则,法律不是专门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况且如何认定“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判定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保护的是守法者,而非所谓的“弱势”群体。离婚时虚构债务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不能在事后靠“卖惨”、“懵懂无知”来推卸责任,法律绝非儿戏,我们不能摈弃基本法律原则,否则将助长虚构债务的行为,产生恶劣的社会导向。
作为法律人,我们呼吁这类案件应以事实为基础、法律为准绳,做出公证裁判方可引导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其敬畏法律的庄严和神圣。因此,我们要提倡事前防范而非事后救济。一方父母若想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应当鼓励其在出资时就向子女及其配偶明确借贷法律关系并立下借据,这才是正确合法的维权路径,而非事后颠覆事实、与子女串通、倒签日期、设计一系列虚假证据,试图以此路径达到维护己方利益的目的。
良法使人行善,恶法使人作恶。“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违法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违法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只要判决尊重客观事实、坚守基本原则,赠与就只能是赠与,而不会因酌情考虑而变成借贷,相信父母及其子女就没有串通造假的市场和空间了。如此才能起到正确的社会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