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公司与贺某签订《经纪合同》,约定A公司为贺某的唯一经纪公司,负责贺某的SNS平台与演艺及公众形象有关的活动。同时合同约定,由A公司注册账号并授权贺某作为宣传、推广平台使用。该账号的运营权限、所有权归属于A公司。贺某在合作期内未经A公司同意不得在非A公司提供或指定的SNS账号上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信息、进行宣传等活动。如贺某经A公司书面催告后,拒绝履行的,A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贺某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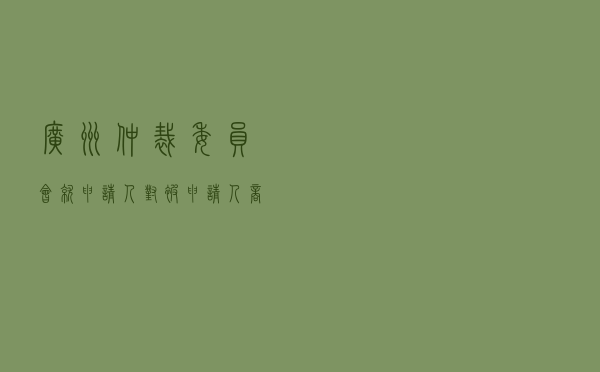
合同签订后,A公司使用贺某的身份信息对其已注册和运营的账号进行了实名认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在双方均无继续合作的意向并就合同终止等事宜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贺某单方变更案涉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并自行登录管理该账号。A公司因此和贺某产生争议:A公司认为其享有案涉账号的使用权;贺某认为其应享有案涉账号的使用权,且A公司不具有获得案涉账号使用权的资格。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1.由第三方运营但经个人实名认证的网络平台帐户的权属;
2.一方可否依据未给另一方造成损失且双方基本达成终止合同意向而主张降低违约金?
【裁决结果】
仲裁庭经审查认定:第一,账号使用权归属于A公司。尽管合同约定了案涉账号的所有权而未约定使用权,但所有权当然包括使用权。同时,根据双方履约期间对账号归属的意思表示,A公司关于账号使用权归属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第二,贺某的行为构成违约,其应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第三,由于贺某并未就A公司欠付《经纪合同》约定的合作收益提出请求,且单方以此抵销合同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仲裁庭不予支持。因A公司未能证明贺某的违约行为给A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仲裁庭酌情调整违约金为30000元,超出部分仲裁庭不予支持。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七十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上述《民法典》四个条文包含了合同无效的情形与合同违约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首先,根据《民法典》与《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简称“《账号管理规定》”),双方可通过合同约定平台账号的归属。其次,《账号管理规定》第三章并未禁止法人注册运营平台账号,故A公司主张使用权并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再次,有关违反合同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简称“《九民纪要》”)中载明,“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鉴于A公司未能证明其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仲裁庭合理向下调整了违约金的数额。
本案系经纪合同纠纷并涉及虚拟财产归属的问题。首先,《民法典》并未将经纪合同纳入“典型合同”中,但学理上认为经纪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而是一种集委托、居间、行纪、培养、宣传、推广、知识产权归属等内容为一体的混合合同”。因此,经纪合同不能完全比照委托合同的规定,而应分别处理合同所涉事项。
其次,平台账号,即“虚拟财产”,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早在21世纪初,我国学界已有关于“虚拟财产”的探讨,并存在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与新型权利说四种主张。本质上,“虚拟财产”无法脱离网络空间而存在,而数据是网络空间的最小组成元素。因此,数据是“虚拟财产”的最基本形式。根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可知,“数据”在我国属于生产要素。进而,通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可推知,数据可作为“物”进行处分。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虚拟财产”并不仅以一种表现形式而存在。因此,需要结合场景对“虚拟财产”上附着的权利、义务与经济利益分别判断,而非仅进行简单归类。就本案而言,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可依据合同约定处分平台账号。然而,处分平台账号并不改变原账号内一方对另一方就具有人身属性财产可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因此,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第十四条,A公司在重新取得平台账号的使用权后,如需再次使用贺某的个人信息,应当重新取得贺某的同意。
最后,尽管贺某违反了合同约定,但按照合同违约损害填补原则,即贺某应赔偿对方因其违约而引起的现实财产的减少,且应赔偿对方因合同履行而得到的履行利益。由于A公司未能证明其损失,故贺某仅需要赔偿自其变更涉案账号手机号后A公司的预期利益。因此,如要求贺某赔偿20万,则会造成明显不公平的情形。
【结语和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其相关联的新型经济模式会不断涌现。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也是全国互联网产业聚集区和电商交易中心,对外开放程度高。如何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对构建经济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就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与归属而言,现有法律未能提供一体适用的答案。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涉“虚拟财产”的争议数量将会不断增加。毋庸置疑,该事项需要法律来进行调整。然而,法律的制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并不是每一个新议题都需要新法律,通过解释进行规则填补亦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方式。然而,现有实践已表明,由于部分“虚拟财产”兼具财产与人身的双重属性,合理平衡个人权益与经济利益是其中的难点与重点。因此,建议就相关类案进行梳理,形成统一的裁决思路作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