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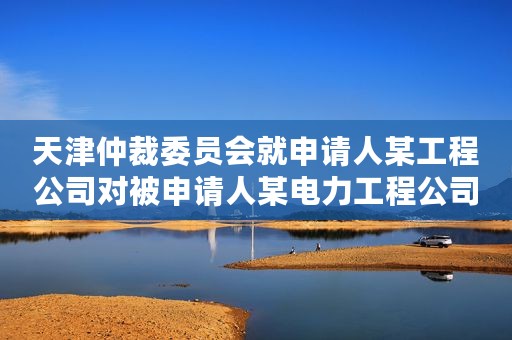
2020年1月2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下称施工分包合同),施工分包合同分为三部分即协议书、合同书(一)、合同书(二)。其中协议书约定:鉴于某某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申请人已经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或专业承包合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工程发包事项协商达成一致订立合同。工程名称: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工程地点:某某县。分包范围:护坡、土方围堰、排水施工。工程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附件一)。施工期限:开工日期2020年1月20日或以申请人书面的开工通知为准。竣工日期2020年2月29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41天。分包合同价款,暂定金额为2,866,899.21元。
2020年1月18日,被申请人出具的《分包单位资金分配计划书》载明,本次收到申请人款项1,415,295元,将用于支付张某某机械款76,220元,周某某运输费30,000元、吴某某机械费10,000元、陈某某机械费90,000元、陈某机械费90,000元,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765,628.6元,某某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费353,446.4元,合计1,415,295元。
2020年1月18日,被申请人出具的《分包单位资金分配计划书》载明,本次收到申请人款项591,505元,支付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2020年1月20日,被申请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申请人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农民工工资(转账)591,505元。
2020年3月23日,被申请人出具的《分包单位资金分配计划书》载明,本次收到申请人款项90,000元,支付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2020年3月31日,被申请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申请人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工程款(转账)90,000元。
2020年6月9日,被申请人出具的《分包单位资金分配计划书》载明,收到申请人款项318,409元,支付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2020年6月10日被申请人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申请人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工程款318,409元。
2020年6月9日,被申请人出具的《分包单位资金分配计划书》载明,收到申请人款项165,000元,支付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2020年6月10日,被申请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申请人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工程款165,000元。
被申请人庭审陈述称,双方包括本案施工分包合同在内共计签订3份分包合同,而申请人付款时,未明确每次付款所对应的合同编号,故被申请人只能对3份分包合同总计收支情况进行统计。被申请人于2020年1月23日收到申请人两笔转款,金额分别是1,586,950元、1,415,295元。2020年6月29日收到申请人两笔转款,金额分别是185,000元、165,000元,以上四笔合计3,352,245元。被申请人收款后,分别向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某某工程机械租赁中心、张某某、陈某某、周某某、陈某某、吴某某、费某某、钱某及陈某等转款,总计转出款项3,121,465元,被申请人留有余额200,780元。
申请人庭后提交的书面说明称“除申请人直接向被申请人汇的四笔款外,其他款项由申请人直接向农民工支付”。
2020年11月1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送达关于履行某某码头改扩建项目建设工程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催办函,催办函称“贵我双方就某某码头改扩建工程,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54、20-1-130、20-1-212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含农民工工资),贵司于2020年7月2日退场。贵司退场后未及时结清农民工工资,导致近期农民工多次到我方项目部及建设单位讨薪……请贵司自收到本函后三日来与我司联系,并办理农民工工资确认、支付事宜。”
再查,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梅某某受案外人周某委托与申请人员工胡某某多次微信联系,二人对包括本案合同项下的分包工程在内的灌注桩及护坡工程分包进行协商,确定让案外人周某借用被申请人资质中标,再通过被申请人转账支付实际施工人的各项费用。
2020年10月17日,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马某某与案外人周某通话,案外人周某在通话时两次提及其借用被申请人资质。
另查,案外人某某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申请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2月8日在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笔录载明,申请人(系该案被告)将编号为20-1-103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作为已方证据之一提交法庭,被申请人(系该案第三人)对该合同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周某仅是借用第三人的名义与被告签订该份合同,第三人仅为资质的出借方,合同签订的目的仅为资质的出借,实际的施工人是周某即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主张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转包违约金1,433,449.61元、信访滋事违约金430,034.88元、退场违约金573,379.84元;2.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违约退场给申请人造成的替代施工增加费用467,500元;3.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超付工程款1,756,167元。
【争议焦点】
施工分包合同是否有效?
【裁决结果】
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案涉施工分包合同是否有效。
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申请人主张其出借资质给案外人周某,周某借用被申请人名义与申请人签订施工分包合同,申请人明知周某与被申请人系挂靠关系,施工分包合同不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施工分包合同无效。申请人庭审时认可其知道案外人周某挂靠被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名义与其签订施工分包合同,施工分包合同实际由周某履行。仲裁庭查明,在施工分包合同签订前,申请人员工同意案外人周某借用被申请人名义与申请人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周某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二次谈话时也提到其借用被申请人名义,该法定代表人未表异议。施工分包合同项下项目亦由周某雇佣的农民工实际施工完成,申请人将工程款先支付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再转给周某指定的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或直接清偿周某所欠的的施工机械租赁费、各项运费等。
据此,仲裁庭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被申请人允许自然人周某使用其名义与申请人签订施工分包合同,而申请人亦明知周某系借用有资质的被申请人名义与其签订合同,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均存在过错,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违反上述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
(2)本案是否适用“有利追溯”原则
仲裁庭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于2020年12月29日公布了新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其第一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由此可见,根据《民法典》制定的新司法解释仍然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无效,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订立的合同,依据《民法典》及新司法解释仍应认定无效,故本案不存在适用“有利追溯”的情形。
【结语和建议】
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工程承包人为了达到发包人招标文件或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对某项工程施工资质的要求,往往借用其他企业施工资质,以被借用资质企业名义投标或签订施工承包(分包)合同,但工程由借用人实际施工,借用名义行为在裁决时给予负面评价,一般没有太多争议,但被借用人与发包(承包)人签订的承包(分包)合同是否一律认定无效,往往会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如发包(承包)人明知或应知被借用人出借资质、名义,仍与被借用人签订承包(分包)合同,而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却与借用人或其雇佣人员直接进行交往,此举表明发包人与名义承包(分包)人均存在规避施工资质管理的过错,违反了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类合同应认定无效。但如果发包(承包)人并不知晓被借用人出借资质、名义一事,而与被借用人签订合同,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始终认为现场施工人员均为被借用人的员工,不知道有借用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违规行为只发生在被借用人和借用人之间,发包(承包)人不知情,不应认定发包人与被借用人签订的发包(承包)合同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