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某经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公司”),被申请人系某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 2018年11月3日,被申请人因资产重组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某段公路收费权进行价值评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对该公路20年收费权进行了价值评估,并于2018年12月25日出具了《车辆通行费收费权项目收益现值评估报告》(以下称“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主要载明:某段公路20年收费权现值评估值为人民币6亿元;某高速路按交通部规划于20XX年建成通车,该条高速公路与涉案公路平行,两线相距较近,该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分流60%车流量……;本次评估综合以上因素选取分流比例为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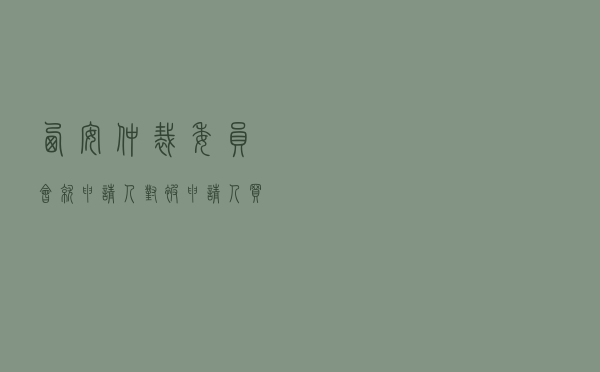
2019年4月11日,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某公路资产重组合同书》(以下称“重组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同时约定该重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报某省交通厅审查批准后生效。该《重组合同书》还在甲方(被申请人)的义务中明确约定:“在某公路部分收费权转让期内,甲方保证某公路未达到设计交通量前,在某公路两侧20公里范围内不再新建给该公路造成分流且与该公路平行的二级以上的公路,但国家规划建设的XX至XX高速公路不受此限制。”2019年8月11日,某省交通厅与申请人签订《XX至XX一级公路收费权转让协议》(以下称“《收费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某省交通厅按照《评估报告》中6亿元的70%即人民币4.2亿万元,向申请人转让某公路20年70%收费权;由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共同组建专门从事某公路收费权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收费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申请人分批、分期向被申请人支付了约定的转让金支付义务。按照《收费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组建的发展公司于2019年10月7日登记设立,申请人出资占该公司70%股份,被申请人以收费权方式投入,占30%股份。
2019年,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2020年4月30日,被申请人与发展公司就某高速公路与涉案公路提前3年通车给发展公司造成的损失及补偿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报省交通厅批准后生效。2020年6月23日,某省交通厅作出批复,同意因高速公路提前建设而给予发展公司进行适当补偿,经济补偿从涉案高速公路建设实际通车之日算至2020年底。发展公司已获得补偿金1.2亿元,该公司2020年10月29日召开股东会对该补偿金进行了分配,后被申请人于2020年11月分两次将申请人应获得的8000万元支付给了申请人。2021年1月14日,发展公司在向某省交通厅提交《关于按实际分流收入给予发展公司经济补偿的请示》中提出:“……经公司董事会多次研究,双方股东多次协商,认为应按实际分流减少的收入给予发展公司经济补偿……”2021年1月18日,被申请人在向某省交通厅《关于落实某公路大修资金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发展公司意见,某高速公路提前通车3年1个月,应当对分流车辆对公司造成的通行费损失按实际因分流造成的收入减少,给予足额的经济补偿……原已补偿金额为1.2亿元,本次应补偿数额为1.9亿元……,被申请人认为发展公司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以解决某公路大修工程资金。
由于补偿问题一直未予落实,申请人和发展公司与被申请人多次进行沟通与磋商,要求足额落实经济补偿因,但一直未有结果,故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认为申请人与某省交通厅签订的《转让协议》及与被申请人签订《重组合同书》,皆以被申请人提供《评估报告》)为基础依据,正是基于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评估报告》中所陈述事实的信赖,申请人才与被申请人达成协议。根据《评估报告》所述,某高速公路提前通车,比《评估报告》中的通车时间提前了3年零25天,该段公路的提前通车造成了车辆的提前分流,并给申请人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此请求:1.裁令被申请人还应补偿申请人因某公路提前三年通车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1.3亿元;2.裁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被申请人答辩认为:1.其并非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故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进行补偿。2.主体资格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不适格,即使有证据证明存在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某省交通厅委托被申请人的行为,行为后果也应由委托人承担,因此被申请人并不适格;而有关收费权的主体是发展公司,申请人仅是发展公司股东,其股东代位行为仅存在于发展公司且公司的有关行为侵害了股东权益的情形,申请人作为发展公司股东作为本案的主体不适格。
【争议焦点】
申请人作为发展公司的股东,能否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发展公司提起仲裁?
【裁决结果】
基于上述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偿发展公司损失1.3亿元。逾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迟延补偿责任。
二、仲裁费XXXX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已由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在履行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时一并给付申请人。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申请人作为发展公司的股东,能否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发展公司提起仲裁?
就本案而言,某高速公路提前通车给发展公司造成了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对此被申请人和某省交通厅也都是认可的,唯独在赔偿数额和申请人能否代表发展公司提起仲裁问题上存有争议。现行《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在公司受损而怠于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股东有权代表公司通过诉讼程序要求侵权或违约的公司高管或其他人承担赔偿责任,尽管法律条文规定的是“诉讼”,但对此应作扩大解释将“仲裁”也包括在内。股东代表诉讼能否以“仲裁”方式实现?
在具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适用情形下,原告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是“诉讼”,这一点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也有明确规定,由此产生的疑问是,能否通过“仲裁”方式来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争议,也即,诉讼是解决股东代表诉讼纠纷的唯一路径,还是仅仅为选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代表诉讼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股东的诉权来源于《公司法》第 151条,该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只是赋予了股东通过诉讼解决相关纠纷的权利,股东代表公司进行仲裁无法律依据,股东代表公司启动仲裁程序时,仲裁机构没有仲裁管辖权,即不承认股东可以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如果公司或股东与侵害公司权益的第三人之间存在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约定,则股东不能依据《公司法》第 151 条到法院主张权利,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有效仲裁协议对解决实体争议的双方有约束力,股东应该依据仲裁协议通过仲裁程序而非诉讼程序为公司的利益主张权利,即不但认可股东代表诉讼可以通过仲裁程解决,而且在约定仲裁的情况下,只能以仲裁方式解决。仅从字面来看,现行《公司法》第151的股东代表诉讼条款的确仅规定了“诉讼”而没有规定仲裁,但是从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出发,股东代表诉讼旨在给权益受到侵犯的小股东提供一个特殊的保护,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本点在于让小股东逾越控股股东或被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法人的障碍,直接向公司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如果将《公司法》第 151 条的规定理解为当事人仅能通过法院以诉讼程序进行救济,而不承认按照仲裁协议享有的仲裁请求权,则会造成以下问题:
第一,架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如果不承认股东代表诉讼可以通过仲裁程序解决,那么在公司与第三人(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或侵权人)就有关债务(或债务纠纷)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事前签订的仲裁协议或纠纷产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就会将欲代表公司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股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公司法》第151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仅限于以“诉讼”程序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因此即使存在仲裁协议也不能选择仲裁解决;另一方面,当股东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第三人如果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由向法院提起管辖异议,在该协议不能被证明是无效的情形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于解决纠纷的选择权,即应当告知当事人提起仲裁,而不能选择诉讼。由此造成的的结果就是:在公司或股东与第三人存在仲裁协议的情况下,欲代表公司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股东既不能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也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从而使得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也架空了《公司法》第151条设置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因此应对这里的“诉讼”作广义解释,即既包括当事人在法院通过诉讼主张民事权利和救济的权利,也包括当事人的仲裁请求权,惟有如此,权利遭到侵犯的小股东可以据此启动“股东代表仲裁”,可以通过仲裁程序为公司的利益直接向公司的债务人主张权利。
第二,剥夺当事人选择解决争议方式权利。仲裁作为解决商事争议的模式,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确认。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因此,对于公司与他人发生的违约或侵权纠纷,公司和第三人均有权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即有权通过订立仲裁条款排除法院的管辖。但如果将《公司法》第 151 条的规定理解为当事人仅能通过法院以诉讼程序进行救济,而不承认按照仲裁协议享有的仲裁请求权,那么就剥夺了当事人依据《仲裁法》本应享有的仲裁权益。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争议解决条款是合同的实质性条款,仲裁条款体现了当事人的重要的商业考虑和商业利益,因此也间接地会影响当事人的商业利益,这有违《公司法》 151 条的立法本意。该条的本意和重点是给小股东一个特别的救济机会和救济渠道,而不是要限制当事人的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因此应对这里的“诉讼”作广义解释,即既包括当事人在法院通过诉讼主张民事权利和救济的权利,也包括当事人的仲裁请求权。
因此,股东代表仲裁与股东代表诉讼在本质上相同的,都是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时,股东得以自己名义代表公司启动并将所得赔偿直接归于公司的一种权利救济手段。股东代表仲裁机制比股东代表诉讼机制更具程序效益,是公平正义精神在程序法中的应然结果。公司代表诉讼的时效性一般较滞后、管辖权受法律约束,程序繁琐,提起诉讼的资格要求严格。仲裁则灵活、简便,体现当事人充分的意识自由、程序上一裁终局的特点。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不占用公共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反映无讼是求的法治传统。就公司而言,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程序也意味着默认中介机构的自由处分权力,避免公司权益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本案中,在发展公司遭受损失并未积极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情况,申请人作为发展公司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发展公司提起仲裁符合《公司法》和《仲裁法》的规定,也即申请人有权提起仲裁申请,其主体资格是适格的。
【结语和建议】
《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于这里的“诉讼”应为仅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还是可以将与诉讼具有同样性质的“仲裁”也包括在内,法律规定不明,理论认识不一,司法实践也有不同判例。这一问题对于《公司法》第151条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的有效实现,以及公司权益的周到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案仲裁庭通过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解释,对于以仲裁方式解决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股东代表诉讼理论及制度的丰富和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