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6年1月18日,申请人A合伙企业与目标公司、被申请人B某及其他八方签订《增资协议》,约定申请人以现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以每股人民币9元的认购价格认缴目标公司新增的人民币2,222,222元出资额,剩余款项作为增资溢价款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申请人将持有目标10%的股权。同日,申请人与目标公司、被申请人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2016年会计年度目标公司的净利润在人民币1,400万元以下,则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总股本的5%的股份。《补充协议》还约定,若目标公司2017年未实现新三板做市商交易,则被申请人同意按年化收益率12%回购申请人股权。2016年2月1日,申请人向目标公司账户转入人民币2,000万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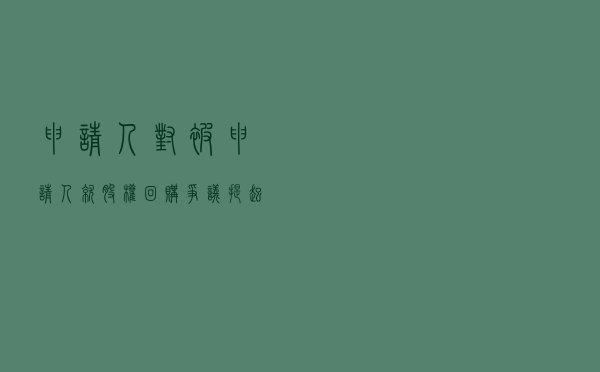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目标公司未能在2017年实现新三板做市商交易,申请人认为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其有权要求被申请人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故依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于2018年1月24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并支付股权回购款。被申请人则认为,由于2016年底股转系统对做市商进行了重大调整,目标公司未能实现新三板做市商交易是基于商业风险因素,系无法预估的不可抗力,并非被申请人的责任。
【争议焦点】
因市场变化所引发的商业风险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裁决结果】
(一)被申请人回购申请人持有的目标公司的3,333,222股股权,并向申请人支付股权回购款人民币24,800,000元 (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其后以12%年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回购价款计算公式为人民币2,000万元×(1+0.12×t),t为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年份数,不满一年的,按照实际月份数折算);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
(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37,25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预缴的人民币237,250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被申请人应径付申请人仲裁费人民币237,250元;
(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不可抗力的概念源于罗马法,其具有不受当事人意志支配的特点,是一种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诸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自然现象,以及战争、罢工等社会现象,均属于目前法律体系下不可抗力的范畴。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类似,我国的民法总则以及合同法等法律将不可抗力规定为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的立法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利益,以司法救济方式重新分配合同履行的风险与收益,维护实体正义;二是提示市场主体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虽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但亦不必因不可预测且不可避免的特殊情况会造成负面影响而过于保守,导致错失商业良机。
【结语和建议】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商业风险因素能否构成不可抗力。仲裁庭认为,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显示,目标公司是基于市场变化原因而主动放弃做市商交易,该种市场变化原因并不属于不可抗力,应属于商业因素本身。综合本案事实及仲裁庭的裁判意见,笔者认为,认定商业风险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需分两个步骤进行判断,第一步是意思自治优先,即审查合同当事人是否就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及要件作出了约定,如有约定则从约定处理;第二步是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不可抗力免责条款的情况下,依照不可抗力的法定构成要件进行严格认定,具体分析如下:
(一)意思自治优先。合同法应循“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的意思自治原则,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不可抗力及其免责条款进行了具体约定,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当优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对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作出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若目标公司2017年未实现新三板做市商交易,则被申请人同意按年化收益率12%回购申请人股权。申请人有权选择在回购条件触发后1个月内书面要求被申请人回购申请人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在上述约定的前提下,由于双方签订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未对相关商业风险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行约定,故本案应依照不可抗力的法定构成要件进行分析认定。
(二)不可抗力的法定构成要件。关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理论上分为三种观点,分别是客观说、主观说以及折中说。客观说认为,不可抗力应以事件的性质以及外部特征为标准,凡属于一般人无法避免和防备的重大外部力量,均应认定为不可抗力。主观说认为,不可抗力应当以当事人预见可能性以及预防可能性为标准,凡属于当事人虽尽最大努力仍不能防止其发生的,应认定为不可抗力。折中说认为,应当采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凡属于基于外来因素发生的、当事人以最大谨慎和最大努力仍不能防止的事件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根据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预见属于主观要件,而客观情况及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属于客观要件。由此可见,我国立法例采取的是折中说的观点。
笔者认为,本案被申请人所提到的商业因素属于典型的商业风险,而商业风险在双方无特殊约定的情形下并不构成不可抗力,理由包括:1.不可抗力是一种客观情况。本案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做市商交易并非基于客观情况,而基于被申请人因市场变化而主动放弃的主观意志;2.不可抗力不具有可预见性。被申请人认为,由于2016年底股转系统对做市商进行了重大调整,做市意义不大,许多新三板公司放弃做市转回协议转让,该政策原因不具有可预见性。笔者认为,商业风险本身就是由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能够给商事主体带来损失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但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抗力的不可预见性不可混为一谈。同时,政策调整在证券交易市场当中并不鲜见,虽然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未预见到股转系统政策的具体调整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在客观上无法预见。3.不可抗力是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况。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是指事件的发生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具有必然性。如上所述,本案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做市商交易并非基于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是基于目标公司对股转系统的政策调整及市场变化进行权衡后的主动放弃行为,故上述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所引发的商业风险与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做市商交易之间并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本案所涉及的商业风险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构成不可抗力。仲裁庭未采纳被申请人的关于不可抗力的抗辩意见,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商业风险在交易市场中无处不在,典型的如价格的波动、社会环境的变化、供求关系变化等,这些情况都属于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不可抗力与商业风险的区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是否具有可预见性。一般情况下,商业风险所伴随的变化情况尚未达到异常的程度,合同当事人具有预见的可能性,而不可抗力则不可预见;2.是否具有可归责性。不可抗力基于其不可预见性而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产生违约行为的,可在不可抗力的影响范围内予以免责。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在一般情况下不构成免责事由,合同当事人需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如预见到某种商业风险存在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可在合同中约定相应的免责条款,或归入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一,以避免争议发生后遭受额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