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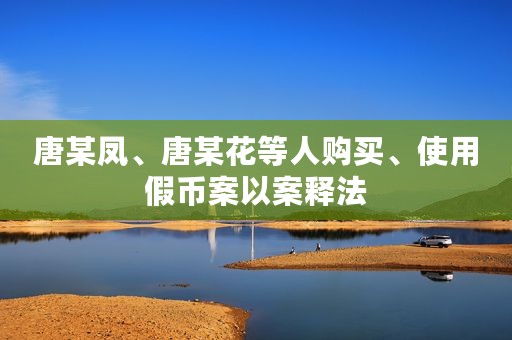
2019年3月至8月被告人唐某凤、唐某花、周某翠等人从被告人李某茂处购买假币总额达70余万元。被告人尹某阔驾车带领4名被告人来到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富裕县、依安县等地区使用假币套取人民币,唐某凤使用假币2600元,唐某花使用假币1500元,周某翠使用假币2800元到达泰来县欲继续使用假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此案在认定事实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现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足以指控事实,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调查与处理】
经依法查明,2019年3月,被告人唐某凤、唐某花各自被被告人李某茂处购买假币10万元,合计假币30万元。被告人尹某阔驾驶租来的小轿车来到辽宁省本溪市、吉林省双辽市等地使用假币,期间尹某阔通过自己支付宝账户将套取的假币汇给了唐某宗、唐某诗、唐岁某等人,同年7月返回沈阳。2019年8月,唐某凤与李某茂联系购买假币,李某茂电话联系被告人邓某昌,邓某昌称自己手里有假币,同年8月10日左右,邓某昌从湖南省道县来到沈阳市将假币28万元出售给李某茂,此日邓某昌经长春返回道县,李某茂电话告知唐某凤假币已送到,几天后,李某茂将面额4.4万元的假币出售给唐某凤、唐某花、周某翠等人。后被告人尹某阔驾车带领4明被告人来到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富裕县、依安县等地区使用假币套取人民币,唐某凤使用假币2600元,唐某花使用假币1500元,周某翠使用假币2800元到达泰来县欲继续使用假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此案在认定事实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现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足以指控事实,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泰来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进行了判决。
【法律分析】
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应为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涉及到货币的印刷、发行、流通、回笼等诸多环节,为保护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所实施的有关管理,每个方面的管理都涉及众多的内容。把包括如此多方面内容的国家货币管理制度视为特有、使用假币罪的客体,就不可能准确的反应其客体的特殊性。因此,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
其一,我国《人民银行法》第3章用多条对人民币做出了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币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有禁止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防止他们进入流通领域的规定。这里,肯定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都指向同一目标,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而不直接指向作为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的货币发行权以及银行出纳管理等。
其二,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由货币的兑换与挑剔、残缺污损货币的处理、禁止伪造与变造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禁止变相货币的使用等内容组成,其目的是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而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危害实质就在于,通过使用、持有等非法手段使假币进入流通领域或为其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危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对象是伪造的人民币和外币,不包括变造的人民币和外币。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有、使用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持有是指拥有,它表现为主体与某一特定之物的占有状态”。因此,只要伪造的货币为行为人所占有,即实际处于行为人的支配和控制中就可以视为持有。“使用”是指将假币取代真币在经济交易中运用,即用于流通,如正常的买卖活动,也有的用作赌资非法活动。同时,以持有、使用的假币达到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的规定,数额较大的起点为四千元。本案中涉案金额已达到70余万元显然已经是数额较大。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货币后又持有或使用的,只构成伪造货币罪,而并不实行数罪并罚,因为持有、使用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不单独构成犯罪,这说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将伪造货币者排除在外。在大多情况下,出售、购买、运输假币者不单独成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但在个别情况又不能把他们排除,因此,确切的说,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伪造货币者以外的自然人主体。本案中所有涉案人员均符合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要求。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明知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明明知道。但要求明知的犯罪,由于其具体内容和认识对象的不同,对主体的明知程度和范围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该罪的明知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解释具有单个性质,因此,它替代不了对持有、使用假币罪中的明知的说明。对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明矢口否认的,总的来讲,要根据假币和持有、使用假币行为的特点以及司法实践经验来确定。具体言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一是被验是假币或者被指明后继续持有、使用的;二是根据行为人的特点(如知识、经验)和假币的特点(仿真度),能够知道自己持有、使用下限币的:三是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等。
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以明知为要件,但不以特定目的为满足。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均可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认定标准。一般来说,行为人明知是假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假币已构成其他假币犯罪的,应当以其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关于收藏为目的的持有假币。以单纯收藏为目的而持有假币的行为,是否成立持有假币罪?或者说,应否将“以使用为目的”作为持有假币罪的主观要件?通说认为,由于刑法并没有要求出于使用目的而持有,假币应属于违禁品,禁止个人收藏,行为人收藏数额较大的假币也会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故只要明知是假币而持有并达到数额较大要求的,就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但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司法解释,行为人购买假币后使用,构成犯罪的,以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不另认定为使用假币罪;但行为人出售、运输假币构成犯罪,同时有使用假币行为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典型意义】
假币的泛滥会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甚至酿成经济和社会危机,制售假币,像一个噬血的幽灵,以非法手段剥夺和占有国民财富,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社会信用原则,侵蚀国民经济的健康肌体,形成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毒瘤。
根据《刑法》第172条的规定,持有、使用假币罪的量刑标准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总面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总面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这起案件就警示人们,假币是经济社会公害,无论是制造、出售还是使用,只要达到一定数额,就都是为法律所不容的。一旦犯下了,那就难逃法律的严厉惩罚。也因此,作为我们每个公民,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怎样的心理,都应自觉主动地拒绝假币、远离假币。否则,难免“摊上大事”而追悔莫及。
总而言之,还是应该增强老百姓识别假币的能力。各地区应当结合当地特点,积极探索反假币新思路,坚持多点出击,坚持主题鲜明,坚持做深做细,坚持立足长远,扎实推进反假工作,提升老百姓反假识假能力,避免干扰了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








